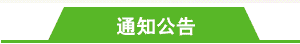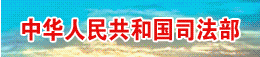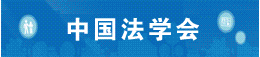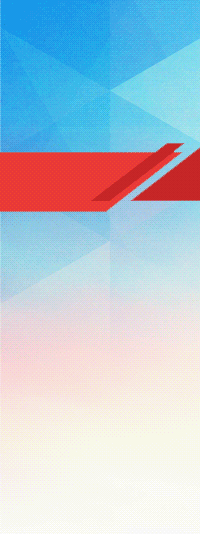
赵建国
碑是写出来的,也是刻出来的。
岁月无声,碑刻能言。碑刻作为文化载体和历史记忆流传至今,镌刻技艺功不可没。
唯有凝神静气,方能走刀如笔。以锋利的刻刀展现软毫书写的效果,绝非易事。下刀稳准狠,刀口方能干净整齐;力道把握全凭经验,用力小了易滑刀,石面刀痕累累,用力大了易崩块,以致前功尽弃。
“透过刀锋看笔锋。”尽管刻的环节往往被忽视,擅刻且擅书法的刻工留名不多,但刻工的书法水准并不能被否认。《峄山碑》的端庄凝重,《曹全碑》的珠圆玉润,《皇甫诞碑》的刚劲不挠……这些碑刻风格多样、各具特色,但无论粗细曲直、方圆刚柔,也无论起笔藏锋的笔画加重,露锋的顺势引入,行笔的稳重顺畅,连带的自然过渡,牵丝的弹性韧劲……在刻工的钢刀下,都能贴切到位,毫厘不爽,非深谙书理者所不能为。不仅如此,刀法的融入、风霜的侵蚀,使这些碑刻更显方峻雄健、挺拔刚劲,平添了不少阳刚气、厚重感。
摩崖石刻“就其山而凿之”。这些摩崖石刻,有的刻在缓坡石坪上,也有的刻在高耸直立的山石上,字体豪放,字径庞大,有的甚至超过一米,极其考验刻工的耐心。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在悬崖绝壁上雕刻。在没有现代化机械的时代,刻工既要发挥聪明才智,更要胆大心细,甚至不惜以身试险。他们有的站在箩筐里,用绳索吊着箩筐,或者直接用绳索吊着自己,也有的在崖壁边上凿几个方孔榫洞,搭建脚手架……身处其中,面前是巨大石壁,脚下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便会跌落山谷。在这样的境地下,还要以錾抵石,以锤击錾。叮当作响,碎石四溅。寒暑不断,兀兀穷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擘窠大字,气势磅礴、雄浑壮观,与周围崇山峻岭、树木葱郁融为一体,其中留存的,岂止是书法精美。
古来刻工皆寂寞,唯有贤者留其名。一块碑,撰写碑文的是文人,书写碑文的是书法家,刻制碑文的,手艺再好,匠人而已。尽管物勒工名,能与文人、书法家相提并论的刻工却寥寥无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明大义识大体。
北宋崇宁年间,蔡京等人为把持朝政,将元祐年间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为奸党,并刻石竖碑立于朝廷端礼门外,史称“元祐党人碑”,后又增至三百零九人,重新刻碑,称“元祐党籍碑”。对这些党人,一律“永不录用”,既不允许其子孙留在京师,也不允许其子孙参加科考。
为了胁迫各地,蔡京后来甚至手书姓名,发往各州县,要求仿京师立碑“扬恶”。在举国上下迫于压力刊刻元祐党人姓名时,令人意外的是,却有两个刻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司马光传》记载,长安石工安民说:“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挥麈录》记载,九江石匠李仲宁说,“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古来匠人身份卑微,寂寂无名,这两位石匠,因为讲了实话、心里话而被载入典籍。青史不欺,道义原不分贵贱高低。
时至今日,手工刻碑愈益减少。经刻工之手共同书写的历史,却永远刻印在我们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