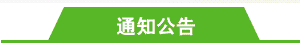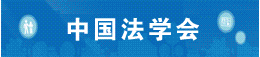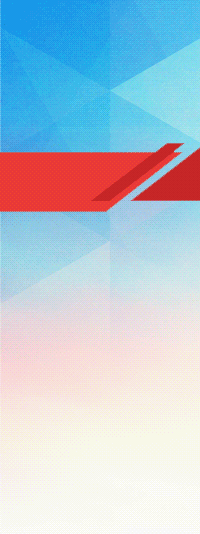

东海版画《浇》 周兴 作
蒋茂龙
“桑木扁担轻又轻,我挑担茶叶出洞庭,船家他问我是哪来的客,我湘江边上种茶人。”这首湖南民歌曾经风靡一时,好似一曲渔歌回荡在美丽丰饶的洞庭湖上。歌词的首句,唱的就是一种劳动工具——扁担。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扁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古人出门,不管是书生赴京赶考、百姓赶集买卖,还是官员他乡就任,对随身物品的携带,首选就是肩挑。
扁担一般用竹子或木头制成,不蔓不枝,扁而长,酷似一个简简单单的“一”字。农村有“柿木案板,槐木椽,桑木扁担用万年”的老话。用木头做扁担,要选用承重能力强、富有弹性的桑木、檀木或上好的榆木。这些木料弯而不折、干不变形、水浸不腐、久放不朽,做成扁担美观,扛在肩头不易磨破肩膀。
我的老家位于平原地带,扁担也是家中常备之物,不过,老家的扁担两头还会装上长度适宜的绳索或铁索,再在末端置以铁钩或木叉钩,我们叫做钩担。名字虽有差别,但共同的任务都是承重、肩负、运输。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小小扁担,混合着木香和尘世的味道,凝聚着劳动者的智慧,也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农人在土地上的所有倾注与收获,都与扁担密不可分。可以说,一根又细又长的扁担,挑起了半部中国农业史,挑来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
“梧桐叶下黄金井,横架辘轳牵素绠。”在儿时的岁月中,乡村的早晨,总是被早起的人们在村中央水井边打水、挑水时碰出的清脆哐当声唤醒。一大家子人和几头牲畜一整天的用水,都要靠扁担一挑子一挑子地往家担,担满了水缸,吃罢了早饭,还要用扁担挑庄稼、挑青草、担粪,每户农家一整天的生活和生产劳动几乎与扁担形影不离。
“早出一扁担,晚归柴满仓。”春天里,为给庄稼地备足农家肥,父辈们用扁担一担担从地头挑到田间。秋日里,扁担是响在田垄上最欢快的口琴,一趟趟地将刚打下的粮食挑到场院里。
由于长年和肩头摩擦,扁担中间部分被汗水浸染,颜色变得极深。整条扁担一如被希望涂亮的日子,总有与众不同的片段。它一路负重前行,走过岁月的河流,响彻在挑担人人生行走的每一句诗行里。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一根扁担闯天下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去,农人们也不再仅仅通过一根扁担,去改变自身的生活和命运。而那负重、承载、无怨的使命精神,却成为后人永远的财富。
肩上扁担,桶中流年。记忆如尘封的扁担,依然坚直,就像父辈们当年的身躯。这种承载着千年薪火的古老工具,坚韧、直行,一头挑起的是命运的奋进,一头挑起的是生活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