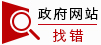以中国特色引领国际实践 以国际视野赋能中国发展
第九届“唐厚志大讲堂”深入探讨仲裁发展前景
法治日报见习记者 薛金丽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 颖
9月16日,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主办的第九届“唐厚志大讲堂”在北京举行。
据悉,唐厚志大讲堂是为了纪念我国仲裁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贸仲资深仲裁员唐厚志先生而设立。本次活动恰逢中国仲裁法施行三十周年和唐厚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中国仲裁周重点活动之一,国内外仲裁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回顾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历程,展望仲裁事业发展前景。
制度变迁:转型现代商事仲裁
贸仲原副主任、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费宗祎担任此次活动的主讲嘉宾。97岁高龄的费老,作为中国仲裁事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回顾了中国商事仲裁去行政化的转型过程。
在1994年仲裁法出台前,中国商事仲裁行政色彩浓厚,机构数量庞大。“当时中国行政部门下设的仲裁机构已经有3000余家,工作人员有两万人之多。1983年至1994年的十余年间,这些机构处理案件200多万件。”费宗祎回忆道,“采取非行政化仲裁模式的只有涉外仲裁机构——贸仲和海仲(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贸仲资深仲裁员、外交学院教授卢松补充道:“当年仲裁机构普遍附设于行政机关内部,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科委的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等。仲裁程序启动不以仲裁协议为前提,实行地域和级别管辖,当事人无选择仲裁机构的自由。”
“1994年颁布的仲裁法被业界评价为进行了‘很大胆的改革’,因为它否定了原有的行政仲裁体系,转向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的现代商事仲裁模式。”费宗祎强调,仲裁法中“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的条款,是“中国仲裁独立公正自主原则的体现”,是仲裁法的“灵魂与核心”。
发展之问:高速如何迈向高质
自仲裁法1995年施行以来,仲裁机构不断增加,仲裁员队伍不断壮大,仲裁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共有仲裁机构285家,仲裁员6万多名,2024年办理案件超60万件,其中涉外仲裁案件4373件。
仲裁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费宗祎坦言,“各地仲裁发展存在不平衡,仲裁机构公信力建设仍然在路上。”
如何解决中国仲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费宗祎提出,应当通盘考虑五个方面:坚持仲裁的独立性、去行政化不动摇;统筹推动仲裁系统性改革落地;通盘构建仲裁员队伍培养制度;进一步明确仲裁机构与仲裁庭的权责边界;坚持走国际化、现代化、本土化并行的中国特色仲裁发展道路。
权责平衡:仲裁庭独立与监督
如何平衡仲裁机构对案件的监督权与仲裁庭的独立裁判权,是机构仲裁模式下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费宗祎观察到,实践中存在两类问题:一是部分仲裁机构受外部干预,将压力传导至仲裁庭,影响裁决公正;二是少数仲裁庭坚持错误裁决,机构却无力纠正。
仲裁机构与仲裁庭究竟是什么关系?机构对仲裁裁决是否负有监督责任?这两个问题成为本次讲堂热议焦点。费宗祎表示,中国实行机构仲裁模式,当事人首先选择仲裁机构,裁决书以机构名义发出,仲裁庭则是“一案一庭”的临时组织,这与英美法系仲裁机构虚位、责任归仲裁庭的模式不同,中国的仲裁机构不仅是程序协助者,更对裁决的最终发出承担责任。
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认为:“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关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服务与保障、监督与支持’的有机统一。”贸仲始终坚持“尊重仲裁庭独立裁决权”的原则,为仲裁庭提供高效的程序支持,同时通过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确保程序合法合规。
融合发展:兼顾本土化国际化
如何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是中国仲裁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费宗祎强调需要警惕一种误区:“不能把西方现代通行的规则奉为圭臬,不能因为中国的仲裁规则跟国际通行的规则存在一些差异,就简单地判定中国现在的规则是落后的。”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东方经验被视为中国仲裁对世界的重要贡献。贸仲资深仲裁员、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律师陶景洲生动地描绘了唐厚志先生在国际会议上“舌战群儒”,推广这一“东方经验”,以及他身体力行地在案件中进行调解的故事,形象地将唐老誉为“唐调解”。
卢松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是解决争议的“两扇门”:一扇门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另一扇门将裁决权交予仲裁员。这种结合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符合商人利益,既灵活高效,又具备终局性,是本土实践与国际仲裁理论深度结合的结晶。
这种立足国情、务实智慧的本土化考量,在仲裁法的制定与修订过程中也有鲜明体现。在立法初期,曾有人建议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标准,规定仲裁协议仅需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即为有效,不必硬性要求当事人事先选定仲裁机构。然而,我国仲裁法最终确立了仲裁协议的“三要素”结构,即除仲裁意思表示外,还明确将“仲裁事项”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列为必要内容。
尽管近年修法过程中,有声音主张简化要件、取消“选定仲裁机构”的要求,但立法机关仍在最新修订中保留了这一规定。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原主任贾东明指出,中国幅员辽阔、仲裁机构数量众多,若未事先明确仲裁机构,待争议发生、双方立场对立之时,再行协商选定机构极易引发分歧,反而增加程序拖延与解决成本,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竞争之钥: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仲裁员素质提升是中国仲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没有高质量的仲裁员,就没有高质量的仲裁裁决”,这是费宗祎对仲裁员队伍建设给出的论断。
仲裁员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操守直接影响仲裁公信力。对此,陶景洲提出中国仲裁员应具备四个层次的能力:处理国内案件、处理涉外案件、在国际案件中处理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件,乃至审理与中国无关的国际案件。他表示,目前国内很多优秀仲裁员已进入第三层次,“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仲裁员跃进第四层次,和国际同行一起处理国际仲裁案件”。
站在“三十而立”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仲裁面临着一项更为艰巨的新使命:实现从规模到地位的质的飞跃。这场新的“攻坚战”路径已经清晰。其基石在于已建立的坚实的制度和丰富的实践。其方法论在于以一种自信而务实的态度,处理好本土实践与国际规范的关系,既要立足国情解决实际问题,又要积极参与并贡献于全球治理体系。而其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则在于能否培养出一批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与顶尖同行同场竞技的仲裁人才。
费宗祎以“壮志未酬身先死,后辈切莫忘初心”缅怀唐厚志先生,同时寄语后辈。这份“初心”,即向社会提供独立、公正、专业、高效的仲裁服务。王承杰为未来擘画仲裁事业发展蓝图时掷地有声:“以中国特色引领国际实践,以国际视野赋能中国发展。”
责任编辑: 朱剑